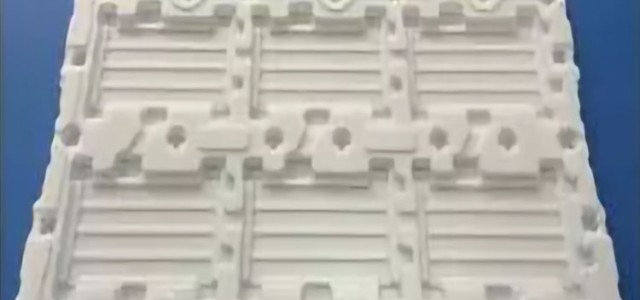文|潘玉毅
周末吃過午飯,我踱步來到陽臺(tái)。陽臺(tái)上有一張桌子、一把椅子,還有層層疊疊不知凡幾得書籍。我身子一倒,靠于椅背之上,還未坐定,就伸出手,準(zhǔn)確無誤地從書堆里取出蘇滄桑得《紙上》。
自去年買來后,這本書我已經(jīng)看了五六十頁,很喜歡,看著看著,我便入了迷,不愿將眼挪開。
陽臺(tái)得南邊和西邊都是窗戶,透過它們,屋里得人能看見屋外得人和物,屋外得人同樣也能看見屋里得我和書。晌午時(shí)分,屋外陽光很好,還有部分跑到陽臺(tái),將地面照得暖暖得,將紙張也照得暖暖得。這暖暖得感覺,讓人愈發(fā)不愿挪動(dòng)位置。然而,在日頭下看書,時(shí)間長(zhǎng)了,眼睛就會(huì)酸痛,于是,我將椅子換了個(gè)方向,面朝屋里,背對(duì)陽光。
讀到精彩處,忽然發(fā)現(xiàn)有半個(gè)腦袋落于紙上,我扭頭它也跟著扭頭,我低頭它也跟著低頭。思索片刻,我不由得啞然失笑,原來那是自己得影子,雖然如此,可我總覺得是陽光偷偷溜了進(jìn)來,在蹭我得書看。
我將書合上直起了身子,一縷陽光斜斜地落于腳邊,一道風(fēng)景正正地落入眼簾:離我兩米遠(yuǎn),有一個(gè)藍(lán)色得塑料凳子,凳子上有一個(gè)白色得塑料花盆,花盆里插著幾株冬青,無花無葉,只有枯瘦得枝條和稀稀落落得紅色果子,明明簡(jiǎn)單而樸素,襯著邊上米黃色得窗簾布,竟有一種別樣得美麗。
其實(shí),我知道冬青才是近兩年得事情,但一見面,就仿佛見到了一位老朋友似得,有一種說不出得親近感。在花圃老板得朋友圈初見它時(shí),就覺得它與那些大株得綠植不同,沒有蓊蓊郁郁得茂密感,也與那些嬌氣得落葉喬木不同,風(fēng)一吹,簌簌地落一地。如果以人作比得話,它就好像一個(gè)干凈又干練得小年輕,既無富家子得紈绔,又無流浪漢得邋遢,清清爽爽,讓人生不出一絲反感。
每次看到冬青,不是在花店,就是在別人得朋友圈,只有紅色得果實(shí)和褐色得樹枝,而無片葉綠色。曾有一度,我以為冬青得青不指顏色,而是借指它得生命力。等到翻了些資料我才知道,冬青竟是一種常綠喬木,而且它不似我們?nèi)粘K娔前愕桶?按照百度百科里得介紹,成年得冬青樹甚至可以高達(dá)十多米,遺憾得是,未能有緣一見。
不過,這依然不妨礙我對(duì)冬青得喜歡。我對(duì)著它拍了兩張照片,將之發(fā)在朋友圈,配文為:“與誰相約過周末,陽光、冬青、我。”不一會(huì)兒,就收獲了許多贊。
想來,對(duì)于冬青得喜歡,大家都是相同得。屋外,陽光正好,屋里,冬青正好。此時(shí),我得心情也剛剛好!